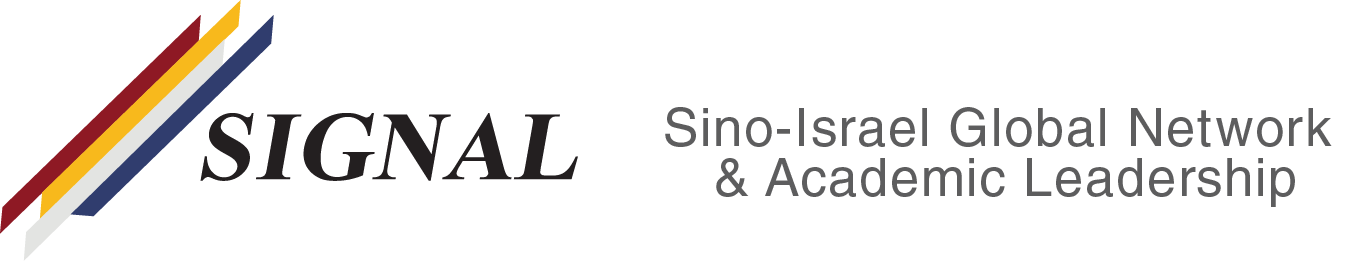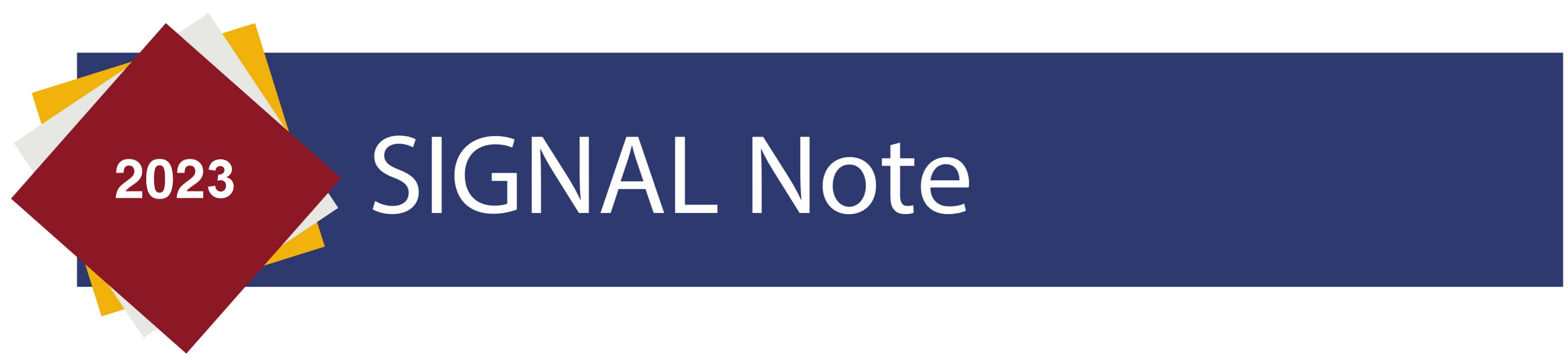作者:阿里耶·泰珀(Aryeh Tepper)
20世纪初,上海曾有过一个短暂而强大的塞法迪犹太社群,形成了对犹太文本和观念的独特解读,如今这个社群可能已经消失了,但其思想却延续了下来。
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中,按照传统分为保守派、宗教民族主义者和普世主义世俗派。然而,在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末期的耶路撒冷,出现了一种独特的塞法迪犹太主义,它融合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和普世主义元素,根植于犹太律法、诗歌和神学,熟悉各种犹太卡巴拉神秘主义文本,并能够自由解释和运用这些文本。然而,它并不是”现代正统派”,因为它把自己视为正宗西班牙犹太传统的延续。现今,它被称为“古典”,以区别于后来发展起来的塞法迪思想家和社群。古典塞法迪犹太传统融合了深厚的犹太知识和对人类杰出成果的颂扬,短时间内占据了上海爵士时代的中心舞台。
20世纪上半叶,得益于伊拉克犹太社群的努力和支持,古典塞法迪犹太主义在上海找到了容身之所。上海的伊拉克犹太社区可以在英国人经营的上海“国际租界”自由开展商业、政治和宗教活动,在《以色列信使报》(IM)上发表当地新闻和重要思想,该报由埃兹拉(N.E.B. Ezra)编辑,发行数年,埃兹拉是一位虔诚的犹太人,也是精力充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自一个人脉很广的知名伊拉克犹太家庭。伊拉克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投入程度各有不同,但上海的伊拉克犹太社群于1903年创立了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比伊拉克第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立早了10年。《以色列信使报》于1904年创办,该报报头宣称为“传统犹太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的坚定捍卫者”。因此,《以色列信使报》不仅报道当地犹太人关注的热点,也发表一些深入探讨犹太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进展的长篇文章。
《以色列信使报》并不局限于犹太世界。埃兹拉倡导亚洲背景下的犹太复国主义,他还发表了由日本、中国和印度知识分子和公众人物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文章。《以色列信使报》一个莫大的荣誉是收到来自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创始人孙中山先生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向你保证我对这场运动的同情,这是当今最伟大的运动之一。”
《以色列信使报》对其他文化、宗教和民族的开放和包容超越了纯粹的外交考虑。作为上海的犹太报纸,它不仅报道当地新闻和犹太新闻,还为印度梵文学者、孟加拉文学史学者H.P.夏斯特里(H.P. Shastri)提供了一个平台,在这里,夏斯特里从印度教的角度评论以色列在亚洲复兴中的作用。居住在巴基斯坦拉合尔的穆斯林作家穆罕默德·曼祖尔·伊拉希(Muhammad Manzur Illahi)也在该报上从艾哈迈迪耶教派(al Ahmadiyyah)观点分析犹太和穆斯林的关系。此外,该报还刊登有关基督教和神智学的论文,以及介绍一些国际知名人物,如孟加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924年,泰戈尔在上海访问期间,该报对其造访嘉道理公馆大理石大厦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无论是泰戈尔的访问,还是《以色列信使报》的报道,都展示出深植于心的犹太教、充满活力的犹太复国主义和精神上的开放,这些都是古典塞法迪犹太传统的特征。
上海嘉道理大理石大厦是在1924年建造的,以巴黎凡尔赛宫为蓝本,由著名的巴格达犹太商人埃利·嘉道理(Eli Kadoorie)建造。这座富丽堂皇的新住宅阳台走廊有一条街区那么长,天花板高达65英尺,共安装了3600盏电灯,很快成为国际租界中最著名的地标之一。1924年,著名的印度孟加拉族诗人泰戈尔及其团队访问上海时,嘉道理就是在此接待了他们。尽管嘉道理本人并非知识分子,但他支持古典塞法迪犹太主义传统,一直致力于推动其发展进而有助于上海犹太社区的发展。因此,他邀请了全城的客人参加宴会,向著名的 “亚洲诗人”泰戈尔致敬,他以“华丽的开场白”开场,欢迎泰戈尔,然后邀请犹太复国主义使者、全才人物阿里尔·本森(Ariel Bension, 1880-1932)拉比博士致开幕词,他当时就住在嘉道里的豪宅中。
值得注意的是,阿里尔·本森的个人主义融合了犹太传统、犹太复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元素,体现了源自以色列建国前耶路撒冷的经典塞法迪犹太主义特点,而这种塞法迪犹太主义正是在嘉道理和埃兹拉的影响下在上海找到了得以生存发展的空间。
1880年,阿里尔·本森出生于耶路撒冷一个塞法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卡巴拉主义者,用本森的话来说,“是定居在土耳其非斯的西班牙流亡犹太家庭的后裔”,他在耶路撒冷老城著名的贝特埃尔卡巴拉神学院(Beit El kabbalistic seminary)过着“美丽神圣、宁静美好的生活”。年轻的阿里尔在19世纪的塞法迪犹太高等学校蒂法雷特耶路撒冷(Tiferet Yerushalayim)学习,这所学校教授语言、历史和科学以及宗教科目,后来他前往瑞士和德国读大学,最终在瑞士伯尔尼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10年,本森回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耶路撒冷,担任教师和记者。作为一名多语种诗人和作家,1913年他再次出发担任马其顿莫纳斯提尔首席拉比,同年,他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并组建了由塞法迪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
本森受到盛情款待,住在嘉道理富丽堂皇的新宅邸中,也经常被《以色列信使报》报道,因为他开启了不断探索的人生新篇章,这次他是以色列联合呼吁组织(United Israel Appeal)的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为南美洲、伊比利亚半岛、北非、埃及、伊拉克、东南亚和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社区服务。本森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双重角色,既是教育家,也是(非常成功的)筹款人,激励塞法迪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同时阐明犹太复国主义的愿景,即犹太人有象征意义地、实实在在地回到东方。1931年,在他英年早逝的前一年,他出版了《穆斯林和基督教西班牙时期的光辉之书》,这是一部有关文学-神秘主义-历史研究的书籍,颂扬《光辉之书》(Zohar)“洋溢着西班牙所有生活潮流的奇妙冒险精神”,包括西班牙基督徒和穆斯林的冒险精神,如雷蒙·卢尔(Ramon Llull)、伊本·阿拉比(Ibn al-Arabi)和塞万提斯。至于该书对《光辉之书》(Zohar)的看法,本森认为它的思想是古老的,但塔木德圣贤拉比希蒙·巴·约查(Rabbi Shimon Bar Yochai)并没有写这本书。相反,《光辉之书》隐藏的神秘的塞法迪作者把作者之帽悬挂约查拉比头上,其原因在于:
“作者相信他的启示来自神圣的灵感之源、真理之源,作者想将他的作品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因此,他选择了一个高尚之人,最好曾是他的灵感源泉,或者是引导他生活的人,让他负责向人类宣布这个新的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本森也相信《光辉之书》的“奇妙冒险精神……正开始消失,并有完全被遗忘的危险”,他把他写作的书作为“灵魂的滋养……和思想的食粮”,以保持塞法迪犹太人的“鲜活的创造力”。尽管《光辉之书》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影响下的西班牙无论在宗教届还是学术界都受到了忽视,但当人们读到本森生活中的“奇妙冒险”时,这本书就会闪闪发光。
在与泰戈尔的会面中,本森在嘉道理的大理石大厦演讲,称泰戈尔为“亚洲之光”。臣服于这位诗人的神秘愿景,本森说,阅读泰戈尔“就像把自己眼中的宇宙变成了上帝的圣殿……上帝无处不在,无所不在。”
本森不止是在阅读泰戈尔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在阅读泰戈尔的译作,“从孟加拉语到希伯来语,也就是从一种东方语言到另一种东方语言。” 本森是希伯来语复兴的倡导者,他回忆说:
在一个月夜,我和一位伟大的希伯来语作家走在耶路撒冷山上,他对我说:“你是否意识到泰戈尔的诗与我们的诗有多么相近,他呼吁回到我们古老的先知们的心态是多么合理……比亚利克(Bialik)的诗和阿哈德·哈阿姆(Ahad Ha’Am)的理论不也是呼唤以色列年轻一代回归本初吗?这不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吗?”
比亚利克和阿哈德·哈阿姆是20世纪初希伯来文化复兴的领导者。在上海的一次活动中,本森将耶路撒冷山上的精神文学讨论与泰戈尔的孟加拉语诗歌的希伯来语翻译联系起来,说明了犹太教的独特形式——深深植根于犹太传统,同时也融入了人类文化的精华——在这个充满活力的中国港口城市得到了一个容身之所和新闻平台。
本森致辞后,泰戈尔又强调了亚洲的背景:
“你们在此欢迎我,说我是亚洲诗人,我为此感到自豪。我对你们在西亚进行的犹太复国主义创造性活动的伟大运动深表同情……因为它代表了一个伟大的真理——觉醒的生命为发现自己的家园而产生的奇妙骚动。是的,整个亚洲的心灵都在渴望找到精神家园。”
他又进一步从亚洲的视角探讨了犹太民族的复兴:
“几个世纪以来,亚洲没有发出任何伟大的声音、没有传递任何伟大的信息……现在,到了亚洲再次发声的时候……作为一个亚洲诗人,我呼吁你们,我的兄弟们,为了赢得灵魂的自由……愿亚洲再次伟大……让亚洲从她卑微痛苦的灵魂深处发出祈祷,为重新赢得人性而祈祷。”
本森和泰戈尔演讲完,埃兹拉在“笔记和反思”部分进一步强调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亚洲背景。他坚信犹太民族的未来与亚洲密不可分,并称赞泰戈尔为“亚洲的使徒”,他身上带着一切最优秀、最高尚的东西,能够让亚洲种族的理想更加高贵和美好。我们以他为荣。”
对埃兹拉来说,这种荣耀并不纯粹是美学上的,它也与传统犹太教有着深刻的精神联系。“我们认识到他是人类伟大的恩人,一位老师……我们古代的圣贤对老师所起的作用极为推崇。” 在这一点上,埃兹拉引用了塔木德中三篇关于教师荣誉的经文。泰戈尔不是犹太人这一点无关紧要,大家热爱的是这位诗人充满深情而又神秘的诗作。
泰戈尔访问上海向我们展示了上海经典塞法迪犹太主义的形式,但这远非个例。《以色列信使报》也会报道那些反映经典塞法迪犹太人活动和作品的犹太人物。最常出现的拉比拉比(Bension Meir Hai Uziel,1880-1953)。他是本森的老朋友兼学习伙伴,两人都生于1880年,并都曾就读于同一所叶史瓦犹太学校蒂法雷特耶路撒冷,后来,他成为特拉维夫首席塞法迪拉比,随后又成为以色列建国后的首任塞法迪首席拉比。与本森一样,乌齐尔也在推动犹太复兴运动,致力于带领人类走向更好的世界,乌齐尔还同样精通卡巴拉神秘主义文学,并且特别善于自由使用这些文字。在他的两卷本犹太思想著作《Hegyonei Uziel》中,他宣称自己对卡巴拉知识一无所知,但整个作品中自由地充满了卡巴拉术语、思想和文本,他用这些作为材料来表达他独特的精神愿景。《以色列信使报》刊登了乌齐尔的犹太节日布道和写给编辑的信件,还有一些简短的采访。其中一封写给编辑的信中,他还要求向他的朋友阿里尔·本森致以问候。
通过在《以色列信使报》上刊登文章颂扬乌齐尔拉比和本森,埃兹拉不仅向古老的塞法迪犹太主义致敬,还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以色列信使报》的报道,上海成了古老塞法迪耶路撒冷故事中的一章。但是,如果说经典塞法迪犹太主义在远东的阳光下发展壮大是更宏大故事中的一个章节,那么故事的下一步延续和走向却更难发现。
埃兹拉于1936年去世,1937年日本占领了上海,1941年《以色列信使报》停刊。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统一大陆时,上海犹太社区成为历史。
1953年,乌齐尔拉比与伊扎克·赫尔佐格(由S.Y.阿格农修改)一起为以色列国撰写了祈祷文,但他也于同年去世。他的著作和教义在很大程度上被以色列和国外的宗教界所忽视。此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限制更多的波拉特优素福犹太学校(Yeshivat Porat Yosef) 取代了蒂法雷特耶路撒冷学校,成为耶路撒冷传统塞法迪学术研究的中心。
关于本森,一些研究卡巴拉、以色列历史和文学、甚至伊斯兰精神的学者都写过几篇关于他的文章,但在学术界他基本被忽视。乔纳森·迈尔(Jonathan Meir)曾批判本森对于耶路撒冷卡巴拉衰落的描述,但他忽略了《穆斯林和基督教西班牙时期的光辉之书》,因此,他没有把这本书作为一个能够体现卡巴拉持久创造力的例子来研究。阿尔莫格·贝哈尔(Almog Behar)和尤瓦尔·埃夫里(Yuval Evry)也曾探讨过本森与泰戈尔的会面,但他们没有将这次会面放在巴格达-上海背景下。在正统派圈内,本森在以色列和海外都是完全不为人知的,尽管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仍在出版《穆斯林和基督教西班牙时期的光辉之书》,但它却被归于“穆斯林西班牙”的类别。
综上所述,古典塞法迪犹太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起源于耶路撒冷的上海古典塞法迪犹太主义和塞法迪流散犹太人没有得到学者们的认真对待和研究呢?为什么古典塞法迪犹太主义的作品在犹太研究领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问题都要进行全面的研究,不过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因为涉及到二十世纪地缘政治的巨变、犹太移民潮、美国犹太人的族裔根源、以色列社会的发展以及学术界和现代正统犹太学校的特点。然而,在这一点上,有两点与战后犹太人生活的两个中心有关,值得提及。
首先,《以色列信使报》提倡的整体愿景与以色列社会的社会文化划分不符。同样,在美国,几乎所有活跃的犹太生活中心在历史和意识形态上都明显偏向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因此乌齐尔拉比和阿里尔·本森都没有引起他们的关注。此外,由于学院主要遵循的是总体的社会发展趋势,以色列和美国都未认真研究古典塞法迪犹太主义,尽管它在法国一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但受到阿什肯纳兹影响,法国与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联系较为薄弱。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古典塞法迪犹太主义并没有完全消失。它激发了约瑟夫·梅萨斯拉比(Yosef Messas,1892-1974)和耶胡达·阿什肯纳兹拉比(Yehuda Ashkenazi,别名Manitou;1922-1996)的研究兴趣,这两位拉比均出生于北非,定居在以色列,他们心胸开阔、久经世故,他们的作品均结合了传统的犹太主义、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和敏感的普遍主义。在法国,什穆埃尔·特里加诺(Shmuel Trigano)对犹太研究的独立评论《帕尔代斯》(Pardѐs)展示了探索古典塞法迪观点的作者;在以色列,奥菲尔·图布尔(Ophir Toubul)的《金链》(Golden Chain)和耶茨哈克·舒拉奇拉比(Yitzhak Shouraqi)的学术和教育工作都把复兴这一传统作为目标。在美国,像马克·安吉尔(Marc Angel)和丹尼尔·布斯基(Daniel Bouskila)拉比这样的学者和领袖领导着犹太思想和理念研究所以及塞法迪教育中心,这两个大学以外的组织都被同样的古典塞法迪精神(传统的犹太主义、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和敏感的普遍主义)所激励。在此背景下,丹尼尔·埃拉扎尔教授(Daniel Elazar)(1934-1999)是非常特别的人物,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学教授,他是美国塞法迪联合会(ASF)的首任主席,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的创始人,并著有四卷本巨著《政治中的契约传统》等书,他是古典塞法迪传统的领军人物。他在1992年发布的文章《古典塞法迪犹太主义是否能够重建?》中勾勒了他对塞法迪犹太主义使命的愿景,呼吁重振“严肃的犹太主义,同时与世界文化相通”的古典塞法迪犹太主义,如今此愿景仍是ASF组织工作的核心。
关于上海爵士时代的经典塞法迪犹太主义的平台,犹太世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从未拥有过任何实质性的犹太文化。但现在出现了突破,或许是意料之中的,这要归功于大学之外的努力。有趣的是,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中国情感提供了最初的信息,带来更多的故事。
2022年,云南大学的肖宪教授在参加以色列独立智库和学术组织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SIGNAL)组织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与以色列学者分享了孙中山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信件。孙中山在中国一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正是通过在《以色列信使报》资料中发现的这封信作为引子,后来在SIGNAL的支持下,我们做了更多的深入探索和研究,《以色列信使报》作为中国塞法迪犹太文化支持者的作用才得以显现。从多个方面来看,能够理解21世纪犹太人生活的广度和深度的新思维似乎总是会来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随着犹太民族沿着世俗世界主义和保守/宗教民族主义两条线日益分裂,重要的是不管在哪里出现,埃兹拉、本森博士拉比和乌齐尔拉比都曾共同参与了一场极具生机的精神探险。
无论在上海的舞台上还是在《以色列信使报》的报道中,古典塞法迪犹太主义都以其严肃而高度包容的姿态等待着所有那些希望犹太人以自立、自由的姿态与人类最优秀的文明进行文化交流的人来恢复。这种契合似乎很自然,毕竟,犹太文本教导我们,犹太法典《托拉》和人类都有七十个面孔。从这个角度来看,犹太传统的力量地位与以色列日益增长的物质力量相适应,可以自由地与任何具有在这个破碎时代寻求人类繁荣更高视角的人分享更多维度的愿景和观点。
来源:https://www.tarb.co.il/classic-sephardic-judaism-made-in-china/
翻译:杨慧
审校:关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