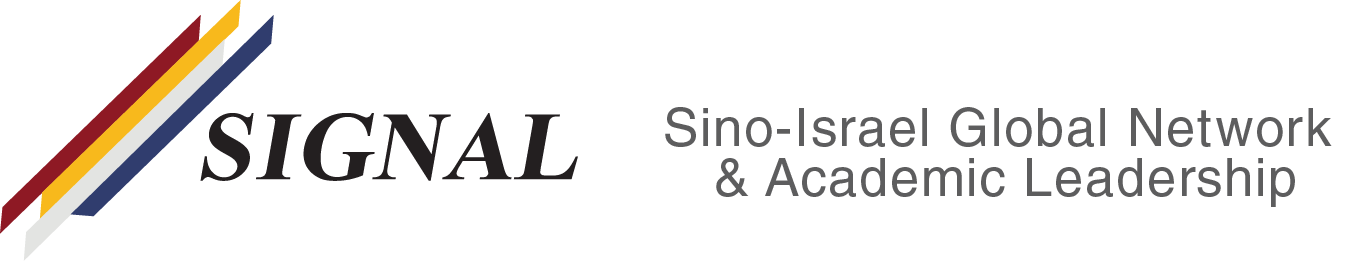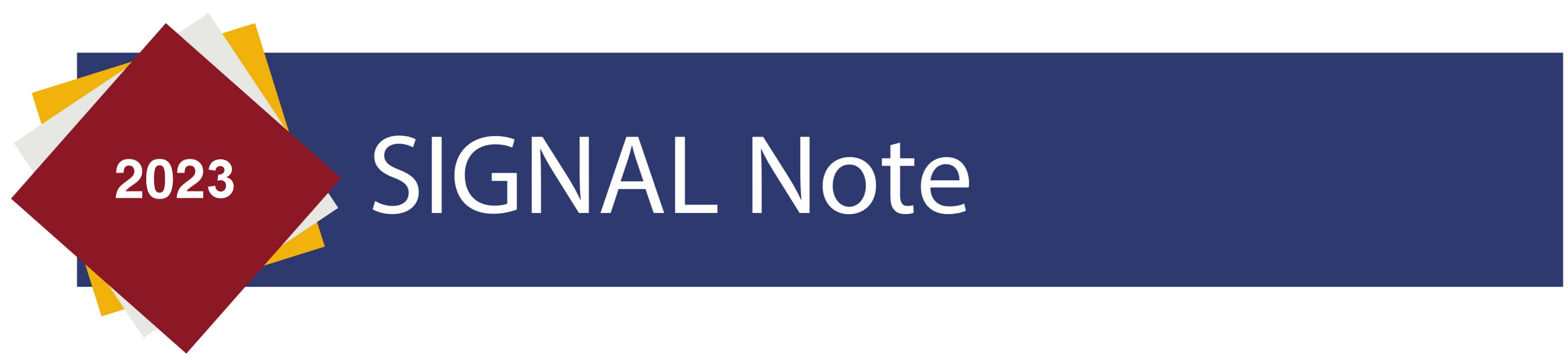塞法迪思想月刊
2023年1月
作者:王达维
新加坡是一个理想的贸易之城,这个国家一向和平,不像中国大陆总是动荡不安。在英国仁政管理之下,商人完全不会经历(中国那样的)跌宕起伏。
——犹太商人约翰·所罗门(John Solomon)1926年从上海到新加坡游览时所记[1]
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上海相似,新加坡高度国际化,经济繁荣,不存在本土反犹主义。然而,与易受中国动荡政治和经济局势影响的上海不同,新加坡是一个和平的殖民前哨地区,位于英属马来亚南部边缘,基本上不会受到亚洲大陆动荡局势的影响,因此新加坡一直都保持“风平浪静”。
新加坡的英国殖民政府为居民社区提供安全保障,其中也包括巴格达犹太人,他们享有殖民统治的自由和保护,大部分投身于商业活动。这种安全保障使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得以在一段时间内推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二战期间,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巴格达犹太人加入了英国一方抵抗日本侵略。战后,在与英国人谈判争取新加坡自治的过程中,一位特别活跃且有影响力的巴格达犹太人发挥了主导作用。
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
1819年,新加坡由托马斯·莱佛士爵士(Sir Thomas Raffles,1781–1826)建立,是东南亚第一个自由港,也是区域贸易和国际海上贸易的主要中心。[2]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当第一位巴格达犹太商人抵达新加坡时,新加坡社会已经高度多样化。岛上三分之二的居民是华裔移民,另三分之一是马来人、印度人、欧洲人、阿拉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3] 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愈来愈多来自欧洲和中东的犹太人来到岛上寻求机会。到1916年,这块殖民地有大约600名犹太人,包括塞法迪东方犹太人和阿什肯纳兹德系犹太人家庭。[4] 该国犹太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达到顶峰,新加坡总人口16万人中有1千人是犹太人。[5]
英国人了解这块宝贵殖民地的战略重要性,赋予其居住人口很大程度上的自由。这种自由和宽容的环境使新加坡成为跨国政治活动的“沃土”。几十年来,新加坡一直是海外华人的政治募款的枢纽,他们为1911年推翻清朝的辛亥革命募集过资金。[6] 巴格达犹太人[7]作为英国殖民者的商业伙伴,从他们抵达的那一刻起,就享有全面的居住许可、公民权和商业特权。[8]在岛上不同社区之间的互动中,反犹主义从未成为敏感因素。[9]和上海一样,新加坡的大多数非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并不熟悉。那些了解它的人,比如中国人,通常对这场运动表现出同情之心。[10]
如同在上海、孟买和加尔各答一样,新加坡最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在殖民地的公民领域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根据殖民地政府的记录,1916年,在500人的名单中,至少有25名犹太人被选为潜在陪审员,但当年殖民地只有600名犹太居民,这个数字非同寻常。这份名单中包括迈耶、埃利亚斯、内森、阿迪斯、本杰明和沙逊家族等著名巴格达家族以及弗兰克尔家族等阿什肯纳兹家族。[11]其中,9人被列为特别陪审员,他们只被要求仲裁一些备受瞩目的案件。这些人包括社区族长、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SZS)主席玛拿西·迈耶(Manasseh Meyer)的儿子鲁本·迈耶(Reuben Meyer),以及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主要成员、历史学家、《以色列之光》杂志编辑埃兹·内森(Eze Nathan)的亲属爱德华·沙逊·内森(Edward Sasson Nathan)。[12] 这些人接受了上流社会的英语教育,属于与英国殖民当局频繁互动的犹太精英圈子。他们对殖民地的公共工程做出了积极贡献:例如,迈耶家族是莱佛士学院(Raffles College)的主要赞助人。[13]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领袖正是出自这些富裕家庭。
1920-1937年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复国主义
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之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当时英国对巴勒斯坦实行托管统治。其发展历史与一位杰出人物——犹太社区族长、岛上殖民地犹太机构的主要赞助者玛拿西·迈耶的参与密切相关。迈耶出生于巴格达,在加尔各答接受教育,在新加坡圣约瑟夫学院继续中学教育。迈耶在孟买工作一段时间后,于1873年回到新加坡,由此在贸易和房地产投资领域开始了自己不凡的职业生涯。作为一名虔诚的正统派犹太教徒,迈耶在德高望重的巴格达拉比约瑟夫·哈伊姆·本·以利亚(Baghdadi Rabbi Yosef Hayyim Ben Elijah)的教导下,坚定地致力于维护圣地的犹太机构。[14] 迈耶与拉比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资助巴勒斯坦的宗教机构。[15]1900年,他带着妻子和七个孩子到耶路撒冷游览,“灌输他们对以色列的爱”。[16]
1920年7月,英国获得巴勒斯坦的托管统治权后,迈耶开始对犹太复国主义感兴趣。爱德华·沙逊·内森(Edward Sasson Nathan)在给总部位于上海的犹太复国主义报纸《以色列信使报》(Israel’s Messenger)编辑以斯拉(N.E.B.Ezra)的一封信中报道,新加坡犹太社区的主要成员在迈耶的住所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决定响应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SZA)的号召,在本地成立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分支机构。迈耶被全票推选为主席,他一直担任这一职位直到于1930年去世。[17]
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第一次会议还向犹太国民基金(JNF)捐赠了1万叻币(相当于今天的8.85万美元)[18],其中迈耶贡献了捐献总额的一半(5000叻币)。此外,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商界的知名人士亚伯拉罕·弗兰克尔(Abraham Frankel)捐款3000叻币。其余款项来自约瑟夫·利维(Joseph Levy,副主席)、艾萨克·迈耶(Isaac Meyer,名誉司库,玛拿西·迈耶之子)、查尔斯·金斯伯格(Charles Ginsburg,名誉秘书,1922-1928年)和爱德华·内森(Edward Nathan)。[19] 这些创始成员在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最活跃的时期(1920-1930年,直到迈耶去世)形成了核心领导层。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协会加倍努力,又筹集了8690叻币。[20]与此同时,玛拿西·迈耶接待了拉比·W·赫希(Rabbi W.Hirsch)的家人。赫希是上海奥赫勒·雷切尔犹太会堂(Ohel Rachel Synagogue)新任命的拉比。他在前往上海的途中在新加坡短暂停留,向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成员发表了“关于犹太复国主义非常有趣的演讲”。[21] 迈耶向所有人开放了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成员资格,并表示愿意在他的豪宅“耶书仑”举办所有会议。[22]在他的坚持下,新加坡成为在东方国家中第一个每年向犹太基金会(Keren Hayesod)捐款的犹太社区。[23]
1921: 以色列·科恩访问新加坡
1921年,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接待了来自犹太复国主义当局的第一位特使。英国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秘书长以色列·科恩(1879-1961)在香港和上海成功完成两次筹款活动后,于2月19日抵达这个岛国殖民地。这些访问是科恩为期一年的亚洲犹太社区之旅的一部分,目的是传播对英国《贝尔福宣言》的认识,并为其实际实现收集“物质支持”。 [24] [25]
和赫希拉比(Rabbi Hirsch)一样,在访问期间,科恩受到了玛拿西·迈耶的热情款待。迈耶在其奥克斯利坡上的豪宅“Belle Vue”里为科恩安排了一个房间,在那里度过的时光给科恩留下了温暖的回忆:
在一个草坡的顶端,坐落着一座富丽堂皇的白色住宅,两侧延伸出宽阔的侧房。迈耶先生戴着一顶黑色无边便帽,坐在扶手椅上,面前的一张小桌子上放着有关希伯来传说的书,他在通往房子正门的门廊等着我。他亲切地向我打招呼,并询问以色列地的和平。[26]
这位远近闻名的犹太族长“被誉为整个远东最富有的犹太人”,但他却如此虔诚和谦逊,科恩感到十分惊讶。迈耶经常访问圣地,他对以色列地非常了解,两人交流了来自以色列地的消息。这位犹太族长还对伊休夫的发展非常感兴趣,他还提到关于采法特和耶路撒冷的塞法迪犹太人被当地阿什肯纳兹犹太人虐待的指控,但特使否认了这一指控。第二天,在去犹太教堂的路上,科恩得知,迈耶在社区是非常活跃的成员,他甚至会发放人力车津贴,确保他资助的圣诺犹太教堂(Chesed-El Synagogue)会众都能全员参加每个安息日仪式。 [27]
次日,为欢迎科恩的到来,迈耶在他的住所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邀请岛上所有成年犹太人参加。演讲在一间“非常大的客厅”举行,一面犹太复国主义旗帜“挂在一面巨大的镀金框镜子上”,十分醒目。大约250人参加了这位犹太复国主义特使的演讲,并对他的筹款请求给予了“热烈的掌声”。讲话结束后,科恩看向迈耶希望他带头发起捐款。[28] 令他高兴的事,这位族长当场开出了一张3000英镑(相当于今天的21.2万美元)的支票。[29]
迈耶3000英镑的捐款是科恩在亚洲访问期间收到的最大一笔捐款。在科恩访问新加坡的剩余时间里,他在犹太社区中的威信和强大的号召力又为犹太国民基金筹集了2000英镑。[30] 科恩表示,总数5000英镑的捐款对这个小社区来说已经是很高的平均水平了。可以公平地说,科恩在新加坡能成功完成使命,离不开迈耶的热情好客、领导才能和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慷慨贡献。
1922:爱因斯坦到访
“我们穿过众多绿色小岛之间的狭窄通道抵达新加坡,受到了犹太复国主义人士的热烈欢迎。” [31]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科恩访问11个月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抵达新加坡进行另一项筹款任务。1922年11月2日,这位著名的物理学家和妻子艾尔莎在前往日本进行巡回演讲的途中来到新加坡这个岛国殖民地。爱因斯坦夫妇此行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目的:敦促新加坡犹太社区最富有的成员向耶路撒冷新建的希伯来大学捐款。筹款会议由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哈伊姆·魏茨曼预先安排,他给玛拿西·迈耶发了电报,要求社区领袖安排招待会。[32]
爱因斯坦夫妇抵达时,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所有领导以及岛上整个犹太社区都来欢迎他们。这次,协会决定在蒙托尔家族的住所接待来访的客人,蒙托尔家族是当地珠宝行业有名的德国犹太家庭。[33] 蒙托尔夫妇还担任爱因斯坦的翻译,方便这对夫妇在访问期间开展社交活动。此外,迈耶的女儿莫泽尔·尼西姆(Mozelle Nissim)作为“最迷人、最能干的女主人”,在迈耶的豪宅安排了一场300人的招待会,豪宅里满是“各式各样的茶点”,同时还有室内管弦乐队的表演。 [34]
当地犹太人普遍对爱因斯坦夫妇十分敬畏并尊重,他们积极响应爱因斯坦的筹款请求。阿尔弗雷德·蒙托尔(Alfred Montor)在宴会上致开幕词时说道:
我们(新加坡犹太社区)认为,接待您是一种崇高的荣誉,您不仅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后代,而且您的才智超越了迄今为止人类所能达到的极限……我们理解您对加快耶路撒冷大学竣工的关切……我们承诺将筹集资金,协助完成这项崇高的工作。[35]
对于犹太社区的热情和主要社区成员给予的隆重接待,爱因斯坦十分感动。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远东(新加坡)看到我们的同胞如此紧密且幸福地团结在一起,感到惊喜不已”。[36]爱因斯坦的筹款请求得到了主持人玛拿西·迈耶的及时回应,他率先向希伯来大学捐款500英镑,随后社区其他人又捐了250英镑。[37]
1923-1930: 筹款势头仍在继续
在玛拿西·迈耶的领导下,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在科恩和爱因斯坦访问后的几年里仍保持着强劲发展势头。1923年,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接待了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哈达萨(Hadassah)[38]代表卡罗琳·格林菲尔德(Caroline Greenfield),她的来访又筹集到来自36名成员3400叻币的捐款。[39]
1924年,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迎来了著名学者、诗人、语言学家艾瑞尔·本森(Ariel Bension)博士,这位学者出生于耶路撒冷,是犹太基金会特使,他用阿拉伯语发表的演讲“给塞法迪犹太人社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获得了6433叻币的捐款。[40] 从1924年到1925年,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又向犹太复国主义基金汇去2175叻币,因而使自1920年以来筹集的资金总额超过一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96.4万美元)。[41] 到1925年底,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成员已达59个。《以色列信使报》评论说,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由一位明智的主席领导”,协会“运转情况良好”,并“为犹太基金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42]
1926年,上海商人约翰·所罗门(John Solomon)前往新加坡的旅途中说,迈耶的住所是“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中心”。他指出,新加坡是“犹太复国主义工作的强大中心,这要归功于像迈耶和金斯伯格、利维等人那样孜孜不倦的工作者”。[43] 事实上,在此期间,名人的领导力仍然是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筹款的一个关键特征。在所有捐款中,迈耶的捐款通常占总额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其余几位协会杰出的领导人也都来自最富有的犹太家族,包括克鲁梅克、埃利亚斯、内森、金斯伯格、利维、蒙托尔和弗朗克尔家族。
从1926年到1928年,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又为犹太国民基金和犹太基金会筹集了2422英镑的捐款。[44] 随着年岁渐长,玛拿西·迈耶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他的女儿莫泽尔·尼西姆(Mozelle Nissim)开始在协会领导层中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以色列信使报》中称,协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尼西姆,称她是“新加坡犹太运动的核心和灵魂”。[45] 在此期间,除筹款之外,创办犹太复国主义杂志等其他举措也提上议程。[46]
1929年3月,当时已病弱的族长玛拿西·迈耶被英王乔治五世授予骑士爵位,以表彰他为新加坡殖民地所做的“公益服务和慈善事迹”,对此新加坡的犹太社区开展了庆祝活动。[47]《以色列信使报》称他为“传统犹太教和犹太民族主义的支柱”。迈耶的名声广受赞誉,包括路透社在内的外国媒体都纷纷刊登了他被授予勋章的新闻。[48]
同时,在他的女儿莫泽尔的领导下,协会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1929年4月,深受爱戴的犹太基金会特使本森博士在族长去世前最后一次访问新加坡。本森的访问让新加坡犹太社区各阶层情绪高涨,作为回报,他们向犹太基金会贡献了高达5000英镑的捐款。[49]同父亲一样,莫泽尔·尼西姆率先发起捐款,捐出3000英镑在沙龙平原附近的克法尔·维特金村(Kfar Vitkin)建立了一所世俗学校,这是巴勒斯坦托管地最北部的犹太人定居点。[50] 剩下的捐款主要来自莫泽尔的两个朋友——协会领导人D.J.伊莱亚斯(D. J. Elias)和维克多·克鲁梅克(Victor Clumeck)的妻子,还有部分来自犹太社区其他人的小额捐款。[51]1929年12月,莫泽尔为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WIZO)新加坡分会成功地组织了一次筹款活动,她担任该组织的主席。[52]
然而,1929年之后,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曾势不可当的筹款步伐几近停滞。1930年,英国对巴勒斯坦政策的逆转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造成了严重的分歧,动摇了富裕的新加坡犹太人和大英帝国其他亲英派上层犹太人的承诺。[53] 此外,1930年帕斯菲尔德白皮书的发表恰逢玛拿西·迈耶去世,他曾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新加坡殖民地筹款的支柱力量。这进一步削弱了协会内部的凝聚力,也动摇了犹太社区对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进一步承诺和发展。
1930年后,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像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一样放慢了筹资步伐。然而,上海出现了大量由俄罗斯和东欧犹太人建立的修正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与上海不同,这种组织没有立刻在新加坡出现。直到1934年,犹太社区才出现下一波政治激进主义浪潮。
大卫·索尔·马歇尔和《以色列之光》杂志
大卫·索尔·马歇尔(David Saul Marshall)于1908年出生在巴格达的一个中上层犹太家庭,长大后成为著名的刑事律师、政治活动家和新加坡第一届民选政府的首席部长。
大卫的母亲弗洛拉曾在巴格达的一所法国精英学校接受教育,这所学校由以色列联合大学赞助。他的父亲索尔也来自巴格达,在新加坡经营着一家成功的贸易企业。[54] 和当时的许多新加坡精英一样,马歇尔中学毕业于著名的莱佛士学院,之后在伦敦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并于1937年被中圣殿学院录取,并被授予律师资格。[55] 在开始他辉煌的政治生涯之前,马歇尔是一位著名的青年活动家,在莱佛士有“年轻的火炬”一称,他对自己的犹太血统持“理想主义态度”。[56] 他与莫泽尔·尼西姆关系十分紧密,曾在莫泽尔家教犹太孩子法语,并时常向她的犹太妇女联盟慈善基金捐款。日军占领期间,莫泽尔留在加尔各答,马歇尔接管了社区领导一职并监管犹太人福利委员会。 [57]
1934年到1937年,马歇尔担任英文杂志《以色列之光》的创始人和执行主编,这是新加坡犹太社区的第一本定期刊物。[58]编辑团队的大部分成员都是马歇尔在莱佛士的朋友,他们是一群来自岛上富裕的巴格达家庭的犹太青年,包括马歇尔的兄弟乔治、沙逊三兄弟、内森两兄弟(包括历史学家埃泽·内森,以及阿迪斯、伊齐基尔和古拜家族成员。[59]
所有这些年轻人都曾在英国的精英学校接受教育,他们将犹太社区的成功视为新加坡国际化精神的象征。正如他们在杂志第一期的社论中所写:“我们社区的人来自世界各地……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些文化。”[60]《以色列之光》的创始人旨在“为当地犹太社区的团结和自尊而努力”,并且“这是对犹太民族传统中一切美好事物的复兴,这是几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一直作为世界之光的复兴”。像他们散居在巴格达的祖先一样,为自己的犹太血统感到自豪,并认为犹太信仰并不是一种障碍,而是形成他们身份的一个重要因素。[61]
与《以色列信使报》不同,马歇尔的《以色列之光》的编辑内容并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而是相对同情这一运动。它向新加坡犹太社区介绍了与世界犹太人有关的严重问题,特别是有关巴勒斯坦政治发展的问题。例如,以色列重印了关于巴勒斯坦的皇家委员会报告,该报告详细说明了圣地复杂而棘手的局势,并建议调整最初的托管条款,以及其他犹太复国主义报纸的各种文章。[62]
这本杂志在亚洲的犹太精英圈子里广为流传,并收到了新加坡社区以外的很多回应。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名誉秘书J·E·萨蒙(J. E. Salmon)在给以斯拉的信中称赞该杂志“在年轻人中大放异彩”。[63] 伊拉克驻孟买领事在给以斯拉的一封信中向他表示,《以色列之光》是伊拉克暂时禁止发行的犹太期刊之一。禁止名单还包括上海的《以色列信使报》和孟买的《孟买犹太论坛报》,这是东方最权威的两份犹太报纸。这一事件表明,该杂志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不仅在亚洲的犹太社区传播,而且还延伸到伊拉克。在那里,其吸引力足以引起伊拉克当局的注意。[64]
1937年,马歇尔辞去了《以色列之光》的编辑职务,开始了他的法律生涯。杂志编辑团队的其他年轻成员也跟随他的脚步,纷纷在新加坡选择了其他职业,于是这本杂志不再出版。1942年,日本入侵新加坡,驱逐了岛上的大部分犹太居民。一些富有的巴格达家庭逃到了美国和印度,而马歇尔选择留下,并作为敌国公民被短暂拘禁在日本营地。在日本占领期间,马歇尔领导犹太福利委员会为新加坡国内流离失所的犹太家庭提供食物和住所,并重新安置来自东欧的犹太难民。[65] 由于缺乏资金、人力资源和组织结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逐渐退出了新加坡犹太人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
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复国主义:特点鲜明
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哪些特点?
我们应该从更广泛的地理文化背景中来看待新加坡犹太人。大量散居的巴格达犹太人将孟买和上海联系起来,展示了他们强大的互联性。据研究东方犹太人的学者西利曼观察,东方的巴格达犹太人有强烈的团结意识,无论他们定居在亚洲的何处,他们都将自己视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单一社区。[66]对于上海和新加坡这两个东亚最大的犹太社区来说,这种互联性促进了他们各自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和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之间的强有力互动。
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和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成员通过《以色列信使报》等英文犹太期刊保持频繁的联系,这些期刊在东部定居点流传广泛。例如,新加坡亚伯拉罕(Abraham)和罗莎·弗兰克尔(Rosa Frankel)的儿子朱利安·弗兰克尔(Julian Frankel)就曾是上海《以色列信使报》的热心读者。用他的话来讲,该报给他带来了“所有犹太人事情的兴奋剂”,并让他对“犹太社区的前景感到欢喜”。[67] 他还曾给该报编辑写信来参与关于犹太事务的公共讨论。[68]同样,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前秘书爱德华·内森曾定期向上海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报道在新加坡进行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爱德华·内森也曾是《以色列信使报》的活跃读者,他称赞该报“在促进远东地区犹太复国主义工作中表现出色”。[69]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还定期在《以色列信使报》上发布年度财务报告,这使得其编辑常常敦促上海效仿新加坡的筹款模式。[70]
与上海的情况类似,新加坡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主要受富裕犹太群体的关注。伦敦和耶路撒冷的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指定其在新加坡的任务以筹款为主,而非招募人力。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像玛拿西·迈耶这样十分富有的犹太人。这种优先考虑实际上将新加坡的大多数普通犹太人排除在他们的筹款策略之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募捐都来源于上层阶级。迈耶有意识地扩大犹太复国主义在精英圈之外的吸引力。他邀请所有社区成员参加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重大聚会,特别是为来访使者举办的盛大接待会,如:以色列·科恩,阿里尔·本森以及爱因斯坦。另外,协会成员会将犹太国民基金捐赠箱放在那些不那么富裕的犹太人家门口,这样他们也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71]
与他们在上海实施的策略类似,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将注意力集中在新加坡最富有的犹太人身上。例如,爱因斯坦访问期间,他只亲自会见了犹太社区的几位主要成员。在其招待会上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这位科学家与十几个人坐在一起:玛拿西·迈耶和他的女儿莫泽尔、儿子鲁本,约瑟夫·利维、伊莱亚斯兄弟、克鲁米克一家、亚伯拉罕·弗兰克尔、查尔斯·金斯伯格、 S. R.沙逊以及以色列· 科恩。[72] 除了科恩被征召到新加坡,作为总统魏茨曼的联络官陪同爱因斯坦夫妇外,其他几位都是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和新加坡犹太社区的主要成员。[73]《以色列信使报》还报道称,在总招待会结束后,莫泽尔为这对科学家夫妇举办了一场40人的私人宴会,是为最有捐款潜力的客人准备的独家活动。[74]
表明上流社会关注新加坡犹太人的犹太复国主义活动还体现在莫泽尔·尼西姆为国际妇女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举办的筹款活动。这次筹款活动在莫泽尔的宅第举行,以日本节日舞蹈和精心安排的茶道为主题。所有与会者都是莫泽尔的女性朋友,如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中主要成员的配偶。不富裕的普通犹太女性未必熟悉这些国际化的元素,也不太可能收到邀请。[75] 这些筹款活动也只用英语进行,毕竟英语是那些接受过英国教育的人的通用语言。1926年,约翰·所罗门(John Solomon)访问新加坡时发现,当地大多数巴格达犹太人都不懂英语。[76]
马歇尔的英文杂志《以色列之光》也与此情况类似。该杂志主要面向上流社会家庭。[77] 其编辑团队只包含那些在英国学校接受教育并且家境富裕的巴格达家庭的孩子。马歇尔的家庭在殖民地中不算最富有,但由于他接受到精英教育,也属于同一上流社会圈。研究新加坡犹太人的学者比德(Bieder)指出,虽然《以色列之光》将人们聚到一起,但其读者主要是生活方式类似于英国殖民精英的同一社会经济阶层的犹太精英,而非他们在马哈拉的教友们 – 当地那些没那么富裕的犹太人浸浴在故乡巴格达的文化、语言和生活方式中,生活在独立的社会中。[78]
少数热心人士推动了犹太复国主义在新加坡巴格达犹太社区的发展。尽管大多数人对巴勒斯坦犹太机构的维护费用表示同情,但仍对犹太复国主义当局持反对、担忧,甚至是批评态度。
早在赫茨尔建立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之前,玛拿西·迈耶和女儿莫泽尔·尼西姆就已经对圣地的犹太社区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迈耶家族是“所有社会机构的支柱”,也是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不可或缺的领导者。迈耶家族所捐款项通常占到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向犹太国民基金和犹太基金会年度捐款的一半以上。迈耶家族的住所是犹太复国主义活动的“活动中心”,莫泽尔则是为所有犹太复国主义使节和访问新加坡的犹太名人举办招待会的女主人。[79] 莫泽尔也是国际妇女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在当地分会的创始人和主席。她是公认的“热心同事以及(迈耶家族)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热烈支持者”,更是“该运动在新加坡的中心和灵魂”。[80]
迈耶家族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投入是犹太复国主义在新加坡筹款活动中取得成功的关键。阿里尔·本森的妻子艾达·本森曾写道,迈耶不仅向所有犹太复国主义基金投入了大额捐款,还利用其权威和影响力来试图动摇犹太社区中“那些冷漠的同胞”,他们“想让这对父女承担社区工作中的大部分工作负担。”[81]
除了迈耶家族之外,新加坡的巴格达精英中很少有人对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展现出始终如一的兴趣。1923年,为卡罗琳·格林菲尔德使团(Caroline Greenfield mission)进行捐款时,捐款达三位数的9名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成员中,爱德华·内森是唯一迈耶家族以外的人。艾萨克斯家族、塞耶斯家族、本杰明、以西结、阿迪斯和古拜斯等家境显赫的巴格达家族只是向犹太复国主义基金提供零星的捐款,却并未加入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核心领导层。[82]
新加坡的犹太人上流社会的某些人没有一直对犹太复国主义给予充分支持,并非出于金钱上的考量。20世纪20年代,新加坡经济蓬勃发展,其金融体系并没有像上海那样受到货币升值或政治局势动荡的影响。同一时期,犹太家族如阿迪西斯家族的房地产持有数量稳步增长,并在20年代末收购了新加坡一些最大的投资组合。[83]
一些富有的巴格达犹太人人对耶路撒冷当局持批评态度,他们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请求无动于衷。1927年,阿卜杜拉·舒克(Abdullah Shooker)是位成功的巴格达商人,也是玛拿西·迈耶集团的前合伙人。在亚历山大·戈尔茨坦(Alexander Goldstein)的募款之旅中,埃兹·内森带着这位使者参观了他的豪宅。由于听说舒克的妻子曾在巴格达和巴勒斯坦资助了一批教育机构,他们希望能从舒克这里得到一大笔捐赠。[84] 然而,舒克却拒绝了来客的请求,理由是他收到一份报告,称住在伊休夫的塞法迪移民遭到了上级阿什肯纳兹人的虐待。[85]
不过,还是有许多人的确在一些场合对这场运动表示同情。若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使者会讲阿拉伯语,会大有帮助。例如,在阿里尔·本森于1924年访问新加坡时,查尔斯·金斯伯格曾这样报道:
“来自犹太基金会的特使本森博士已经抵达这里,我们社区成员对此表示热烈欢迎……本森博士用阿拉伯语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的发言给塞法迪(巴格达)社区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们以前没有机会向他们如此详尽地并令人信服地解释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森博士极具魅力的人格为他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预计他在这里的任务将取得圆满成功。”[86]
本森出生于耶路撒冷,他可以用阿拉伯语进行有效的交流,并且其人格魅力让他的表达更有说服力。尽管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中的上层人士都接受过良好的英语教育,但他们对自己的巴格达身份有着深厚的感情。本森用阿拉伯语发表讲话,展现出了礼貌和尊重,并且此举为他赢得了社区的友好相待,他们向犹太人基金会慷慨捐赠,给予回报。[87] 出于同样的原因,本森在上海巴格达犹太人社区也深受欢迎。因此,在所有犹太复国主义使者的访问中,本森在新加坡的两次访问中募集的款项最多。
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领导层的多元化特征。除乔·伊利亚斯和爱德华·内森之外,迈耶在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许多随行人员及主要捐助者很多都是阿什肯纳兹德系犹太人。其中包括亚伯拉罕·弗兰克尔,一位从事房地产和家具生意的立陶宛-罗马尼亚犹太人,是新加坡最富有的人之一;[88]维克多·克鲁梅克是亚拉伯罕·弗兰克尔的女婿,出生于雅法,在开罗长大;[89]约瑟夫·利维(副主席)是德国出生的酒商;[90]阿尔弗雷德·蒙托尔是出生于德国的珠宝商人;[91]查尔斯·金斯伯格(荣誉秘书,1922-1928)是美国犹太人,也是维克多·克鲁梅克的女婿。[92]
他们的领导力极大提高了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筹款效率。由于会讲德语,阿尔弗雷德·蒙托和妻子安娜在1922年接待了爱因斯坦夫妇,并在他们逗留新加坡期间担任翻译,极大地方便了这对夫妇与当地犹太社区的社会交往。[93]亚拉伯罕·弗兰克尔、维克多·克鲁梅克和约瑟夫·利维是继迈耶夫妇之后,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三大捐赠方。弗兰克尔和克鲁梅克的妻子罗莎和玛丽是莫泽尔·尼西姆的密友,并在她的国际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的当地分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94] 埃兹·内森表示,弗兰克尔和克鲁梅克家族是新加坡“最勤劳、最受欢迎的德系犹太人”。这表明这些位居社会上层的阿什肯纳兹德系犹太人家族在以塞法迪犹太社区为主的新加坡内外都具有广泛的吸引力。[95]
对20世纪20年代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新加坡巴格达犹太人来说,随后的十年里,他们的选择范围有所缩小。1930年,巴勒斯坦局势日益动荡,随之《帕斯菲尔德白皮书》发布,标志着英国政府关于犹太人移民和土地购买的政策发生转变,并给伊休夫地区的政治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英国的决策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的分裂局势,动摇了大英帝国许多上层亲英派犹太人的决心。这些后果也给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造成了影响。
结语:大卫·马歇尔为英国而战并与之谈判
最终,与上海的许多巴格达犹太人一样,新加坡的巴格达犹太人感到必须把对英国的忠诚置于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之上。大卫·马歇尔作为《以色列之光》的编辑,1934年,他曾公开谴责从巴勒斯坦前往新加坡的一位狂热犹太复国主义使者的行为,原因是他指责岛上的犹太家庭没有响应他挨家挨户筹款的呼吁。埃兹·内森表示,新加坡的多数犹太人都赞同马歇尔的观点,并认为所有与圣地有关的决定“都应在社区内部做出”,而且“他们对新加坡和英国的忠诚不应受到质疑”。[9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新加坡的犹太人精英阶层纷纷通过参军入伍以向英国表示效忠。在日本入侵迫在眉睫之时,马歇尔加入了新加坡志愿军,这是英国殖民政府为保卫新加坡而组建的辅助性民兵组织。[97] T.A.D.沙逊是马歇尔在《以色列之光》的另一位编辑团队成员,也是著名的沙逊家族在新加坡的后代,战争爆发时他位于伦敦,并随之加入了皇家空军。[98]埃兹·内森跟随他的朋友一同加入了新加坡的医疗辅助队。这种忠诚也同样在阿什肯纳兹德系犹太人身上得以体现: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的领导人维克多·克鲁梅克之子纳撒尼尔·克鲁梅克加入了印度皇家空军。[99]
他们对英国的忠诚却让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日本占领期间,马歇尔和其他留在新加坡的犹太人作为敌国国民被关押在日本劳改营,饱受营养不良、痢疾和疟疾之苦。一些年轻人则被分配至泰国至缅甸的“死亡铁路”上工作。马歇尔被派往北海道,在一个煤矿工作。[100]
多年以后,作为新加坡首席部长,大卫·马歇尔率领由各党派组成的代表团与英国就殖民地的未来进行谈判,他坚持要求给予新加坡充分的内部自治权,同时要求英国保留对外交政策和对外防御的控制权。[101] 和众多上层犹太人一样,他认为在后殖民时代,英国的保护对于新加坡的独立和生存不可或缺。[102]
翻译: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李雪倩、廖靖倩、王宇昕、李佳、柳无迪
审校:关媛
[1] “The Jews of Singapore: Special Interview with John Solomon,” IM, 2 April 1926, p.21.
[2] Stephen Dobbs, “Singapore” in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Maritime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 “Founding of Modern Singapor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ccessed 4 April 2021,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0508135636/http:/app.www.sg/who/32/Founding-of-Modern-Singapore.asp
[4] Bieder, The Jews of Singapore, 62; “Special Interview with John Solomon,” IM, 2 April 1926, p.21; Cohen, “Jews in Far Off Lands,”: During the colonial era, the community consisted mostly of Sephardim, with a sprinkle of Ashkenazim.
[5] “Letter from AJDC New York to Mr. A. C. Glassgold of Shanghai, Re: Jews in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JDC NY AR194554 / 4 / 64 / 1
[6] Huang Jianli, “Umbilical Ties: The Framing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as the Mother of the Revolution,”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6, no. 2 (2011): 183–228.
[7] 本章我采用“巴格达犹太人”(而不是巴比伦人、伊拉克人或塞法迪人)一词来指代在亚洲殖民地散居的中东犹太人。有关术语的讨论,请参见S.R. Goldstein,《伊拉克哈希姆的巴格达犹太人网络:民族主义时代的犹太跨国主义》(博士论文。莱顿大学,2019),69。
[8] Jonathan Goldstein,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The Trade, Memory, and Transnational Identity of Singapore’s Baghdadi Jews, 1795-2013,” The Journal of Indo-Judaic Studies, no. 13 (2013): 98.
[9] Chan Heng Chee, A Sensation of Independence :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vid Marshall (Singapo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2.
[10] Israel Cohen, The Journal of a Jewish Traveller (London: John Lane, 1925), 203-204
[11] Bieder, The Jews of Singapore, 63.
[12] 同上,62: Eze Nathan后来成为社区历史学家和《新加坡犹太人的历史》( :1830-1945)的作者。
[13] “SIR M. MEYER DIES AT AGE OF 84,” The Straits Times, 1 July 1930, p. 13.
[14] Goldstein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105; David Solomon Sassoon, A History of the Jews in Baghdad (Letchworth: S.D. Sassoon, 1949), 149.
[15] 同上,图5引用于104:Ben Ish Hai为新加坡圣诺犹太教堂的开幕创作了特别的献词,该教堂是迈耶于1905年建造的;科恩,The Journal, 200:梅耶在耶路撒冷为塔木德研究(Beth Ha-midrash)和巴格达犹太人修建了一座犹太教堂。
[16] Goldstein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103-105.
[17] “Singapore Jewish Community Vies with Shanghai in Raising Large Sums,” IM, 16 July 1920, p. 7.
[18] 在本章后面,符号“S$”表示“海峡元”,即1898年至1939年海峡殖民地使用的货币。在20世纪20年代,1海峡元的货币价值大致相当于1英镑的八分之一,在新加坡也广泛流通。
[19] “Large Sums Raised in Singapore,” IM, 16 July 1920, p. 8.
[20] IM, 29 October 1920, p. 17.
[21] IM, 17 December 1920, p. 45.
[22] Bieder, 《新加坡的犹太人》(The Jews of Singapore),31,33:要成为SZS会员,只需每年缴纳S$25(额外的可选捐款范围从10新元到400新元不等)。SZS会议在梅耶位于加东海滨的豪宅举行。”
[23] IM, 7 March 1930, p. 8.
[24] Cohen, The Journal, vii.
[25] 以色列·科恩是出生在曼彻斯特的英国犹太人,1922年起担任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秘书。他在亚洲犹太人社区(包括上海和新加坡)进行了历史性的筹款之旅,从1920年到1921年持续了一年,筹集了超过11.6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900万美元)。他是《犹太旅行者日记》(Journal of A Jewish Traveler)的作者,是英国殖民统治下亚洲犹太人社区为数不多的第一手资料之一。
[26] 出处同上., 199-200.
[27] 出处同上,200-201.
[28] 出处同上,202;在谈到观众的反应时,科恩主要描述了事实。例如,当他看到自己在孟买和加尔各答的演讲出席率很低时,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沮丧之情。见以色列···········科恩《在遥远土地上的犹太人》一文,选自《犹太编年史》,1921年6月3日。
[29] Cohen, A Journal, 202-03.
[30] 出处同上
[31] Albert Einstein and Ze’ev Rosenkranz, The Travel Diaries of Albert Einstein : The Far East, Palestine, and
Spain, 1922–192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111.
[32] IM, 1 December 1922, p. 14.
[33] 出处同上。
[34] 出处同上,“新加坡犹太人对爱因斯坦夫妇的难忘接待”,第17页;《海峡时报》,1922年10月31日,11月3日:招待会于下午5点在梅耶的豪宅举行。与会者包括犹太社区的主要成员和新加坡圣公会主教。
[35] IM, 1 December 1922, p. 17-18; Montor’s speech was also reprinted in local press. See The Straits Times, 3 November 1922.
[36] IM, 1 December 1922, p. 18.
[37] 出处同上。
[38] 哈达萨(美国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是一个美国犹太志愿者妇女组织,由亨利埃塔·索尔德于1912年创立。见https://www.hadassah.org/about/history。
[39] IM, 9 February 1923, p. 19.
[40] IM, 11 April 1924, p. 17; 6 September 1924, p. 14.
[41] IM, 1924年9月6日,第14页;1925年11月6日,第13页;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在1924年向犹太复国主义总部汇款1355英镑,1925年汇款820英镑,其中大部分流向了犹太基金会和犹太国民基金。
[42] 出处同上。引文摘自《以色列信使报》对1924年和1925年新加坡犹太复国主义协会年度报告的评论,这两份报告都发表在该报上。根据1924年的年报,玛拿西·迈耶还担任过犹太基金会新加坡分公司的总裁。
[43] “Jews of Singapore: Special Interview with John Solomon” IM, 2 April, 1926, p. 2.
[44] IM, 6 May 1927, p. 4; 8 July 1927, p. 10; 6 January 1928, p. 21: The SZS raised £800 in 1926, £500 in
January 1927, and £1,122 throughout the rest of 1927.
[45] IM, 6 January 1928, p. 21.
[46] IM, 1928年3月2日,第9页:埃利斯·M·巴苏是一名公关人员和商人,他曾提议创办犹太月刊《犹太标准》,致力于“犹太人、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在海峡定居点的利益”。然而,这一倡议并未得到足够的支持和重视,最终未能取得成果。
[47] “MALAYA’S NEW KNIGHT,” The Straits Times, 1 March 1929, p. 11.
[48] IM, 5 April 1929, p. 54.
[49] IM, 3 May 1929, p. 6.
[50] 出处同上., J. Goldstein,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107; J. Goldstein, Jewish Identitie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 Singapore, Manila, Taipei, Harbin, Shanghai, Rangoon, and Surabaya (Berlin, Germany; Boston, Massachusetts: De Gruyter Oldenbourg), 2015.
[51] IM, 15 May 1929, p. 2.
[52] WIZO于1920年由Rebecca Sieff、Vera Weizmann (Chaim Weizmann的妻子)、Edith Eder、Romana Goodman和Henrietta Irwell在伦敦成立,为巴勒斯坦托管地区的居民提供社区服务。
[53] 参见《帕斯菲尔德白皮书》;正如第二章所讨论的,许多迄今为止对上海巴格达社区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慷慨的富有捐助者,如维克多·沙逊爵士,在看到该运动的目标不再与英国政策一致后,撤回了他们的支持。
[54] Bieder, The Jews of Singapore, 35.
[55] 出处同上,81;第二章李光耀的“成长”,《新加坡故事 :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普伦蒂斯大厅出版社,1998); Tien Mui Mun,《贾拉特南》, Singapore Infopedia, n.d. 2021年5月2日访问:李光耀和拉贾拉特南,两位新加坡的创始人和马歇尔的同事,都在莱佛士接受教育,在开始政治生涯之前在英国获得法律学位。李光耀成为独立后新加坡的长期总理。拉贾拉特南是人民行动党(PAP)的联合创始人,并担任过一系列内阁职位。
[56] Nathan, The History of Jews in Singapore, 81.
[57] Bieder, The Jews of Singapore, 88, 111.
[58] Nathan, The History of Jews in Singapore, 81-82.
[59] Bieder, The Jews of Singapore, 86-88.
[60] Nathan, The History of Jews in Singapore, 81-82.
[61] 出处同上。
[62] Bieder, The Jews of Singapore, 88.
[63] IM, 2 September 1934, p. 19.
[64] M, 1935年6月1日,第16页;《IM》,1935年8月2日,第10页:该杂志后来被允许进入该国,而以色列的《信使》和《犹太论坛报》仍然被禁止;S. R . Goldstein,《巴格达犹太人网络》,187-88:外国犹太人和非犹太人期刊在这一时期在伊拉克犹太社区享有广泛的读者群。在禁止犹太复国主义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对外国媒体的审查发生在英国托管结束和费萨尔国王去世后,该国的动荡和反犹太情绪日益加剧的背景下。
[65] Bieder, The Jews of Singapore, 111.
[66] Jael Miriam Silliman, Jewish Portraits, Indian Frames : Women’s Narratives from a Diaspora of Hope (Calcutta: Seagull Books, 2001), 2–10.
[67] IM, 11 April 1924, p. 22.
[68] IM, 5 August 1927, p. 19.
[69] IM, 5 April 1929, p. 21.
[70] “Singapore Jewish Community Vies with Shanghai in Raising Large Sums,” IM, 16 July 1920, p. 8; IM, 6
September 1924, p. 14; IM, 3 May 1929, p. 6: “Singapore has taken a fine lead and we hope her example will be emulated in Shanghai.”
[71] M, 1924年9月6日,第14页:JNF的箱子在1924年收集了超过S$1595,占当年向JNF定期捐款的八分之一。《以色列信使报》评论说,协会在收集小额个人捐款方面的表现应该可以让上海受到“启迪”。
[72] IM, 1 December 1922, p. 18.
[73] 虽然并不是所有显赫的犹太家庭都出现在SZS的领导层中。请参见下面的部分。
[74] IM, 1 December 1922, p. 18.
[75] IM, 6 December 1929, p. 29
[76] “Special Interview with John Solomon,” IM, 2 April 1926, p. 21.
[77] Bieder, The Jews of Singapore, 86.
[78] 出处同上., 88.
[79] “Special Interview with John Solomon,” IM, 2 April 1926, p. 21.
[80] Ida Bension, “Jewry’s Grand Old Man of the Far East,” IM, 7 March 1930, p. 8; 6 January 1928, p. 21.
[81] I. Bension, “Jewry’s Grand Old Man.”
[82] 《卡罗琳·格林菲尔德抵达新加坡》,IM, 1923年2月9日,第19页;比德尔,《新加坡的犹太人》,87年版:这一页包含了1934年埃利斯·以西结婚礼出席者的合影。据比德尔说,邀请函发给了岛上所有重要的犹太家庭。我交叉比对了出席者名单上的姓氏和深圳大学的捐款记录;有关新加坡殖民地富裕犹太居民的概况,请参阅J.E. Nathan,《英属马来亚人口普查(海峡殖民地、马来联邦州和柔佛、吉打、佩利斯、吉兰丹、丁加奴和文莱的受保护州)》(1921),第91页。
[83] Bieder, The Jews of Singapore, 85.
[84] Nathan, The History of Jews in Singapore, 76-77; J. Goldstein,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107.
[85] Nathan,《犹太人在新加坡的历史》,77:在得知埃兹的父亲埃利亚胡·内森是巴格达社区中受人尊敬的成员后,舒克最终给亚历山大·戈尔茨坦开了一张2000美元的大额支票。
[86] IM, 11 April 1924, p. 17.
[87] See Chapter Two, section 2.2.
[88] Bieder, The Jews of Singapore, 60, 112: 比德尔:《新加坡的犹太人》,第60期,第112期:弗兰克尔一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入侵前前往旧金山。
[89] 内森,《犹太人在新加坡的历史》,63年;比德尔,《新加坡的犹太人》,29岁;丽莎·金斯伯格,《新加坡的不同世界:一个犹太家庭的故事》,《亚洲犹太人的生活》,no.15(2014年10月);维克多·克拉麦克在开罗讲法语的犹太社区长大。他是A. Clouet & Co公司的老板,专门从事食品和建筑材料进口。他娶了亚伯拉罕和罗莎·弗兰克尔的女儿玛丽。
[90] 内森,《犹太人在新加坡的历史》,63岁:约瑟夫·列维是SZS的副总裁,Chandlers & Wine Merchants的老板。他和他的妻子都是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最终移民到巴勒斯坦。
[91] 同上,60:阿尔弗雷德·蒙托的珠宝公司是新加坡金伯利钻石、派克钢笔和露华浓的主要进口商。
[92] 金斯伯格,“新加坡的不同世界”:查理·金斯伯格是维克多和玛丽·布洛克的女婿。
[93] IM, 1 December, p. 17; Einstein, The Travel Diaries, 111-17.
[94] IM, 15 May 1929, p. 2.
[95] Nathan, The History of Jews in Singapore, 62-63.
[96] 同上., 83.
[97] Bieder, The Jews of Singapore, 89.
[98] Nathan, The History of Jews in Singapore, 91.
[99] Bieder, The Jews of Singapore, 93.
[100] 同上., 93, 111.
[101] C. M. Turnbull, History of Modern Singapore : 1819-2005 (Singapore: NUS Press, 2009), 265.
Chan,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David Marshall, 183.
[102] 阿什·达马辛厄姆,《苏伊士以东:英国的亚洲世纪战略》伦敦国王学院毕业论文,2017);在马歇尔和其他新加坡早期领导人的坚持下,自新加坡独立以来,皇家海军一直在新加坡海军基地保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