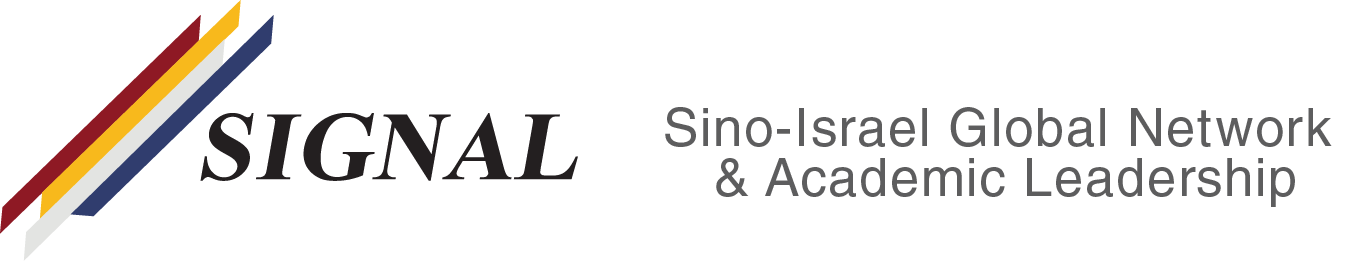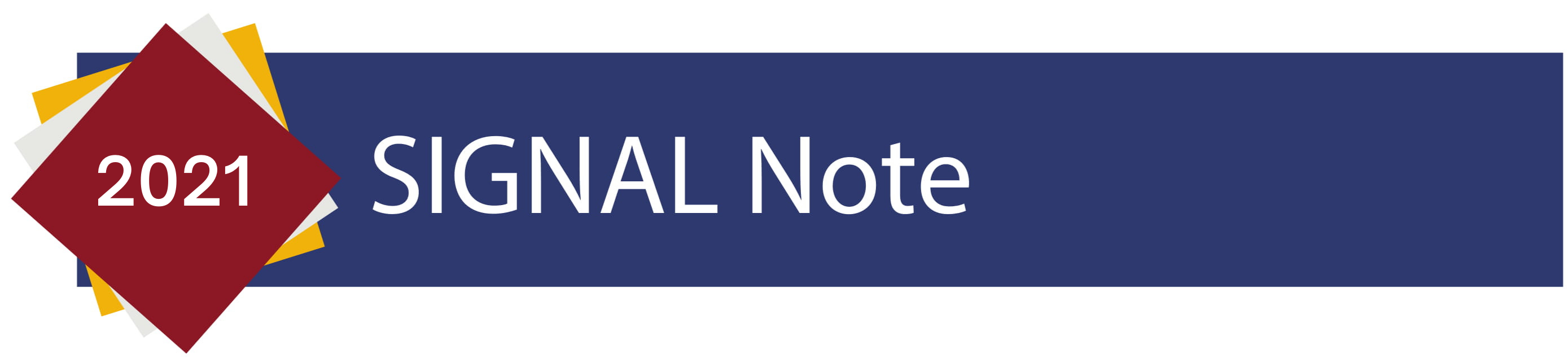第一部分 作者: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 汤米·斯坦纳
本文属于两篇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将对巴以冲突的历史进行深入分析。稍后呈现的第二部分将考察冲突对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
近几个月来,中国对中东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3月下旬,外交部长王毅访问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最近加沙冲突期间,中国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也试图促成停火。王毅外长在联合国再次提出中国主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和谈的提议。王毅还明确表明中国对这场冲突的立场:“巴勒斯坦人民的真诚朋友”,而没有提以色列。他还谴责了联合国过去的决议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的事实。而外交部发言人则更直接将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称作:“站在人类良知和道德的对立面”。
如果中国寻求在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方面发挥领导作用,那么就需要更好地认识形成冲突的主要历史因素。中国外交官或许还会注意到欧洲对这场冲突态度的转变。欧洲传统上一直对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以及以色列使用武力保护其人民的做法持批评态度。但在最近与加沙的冲突中,欧洲表现出对以色列的强烈支持。
然而,世界其他地区的政治领导人、外交官和记者们对这场冲突的看法仍比较浅显,他们认为以色列是这场冲突的 “罪魁祸首”。这种简化的观点与另一种流行说法密切相关,即巴以冲突是中东冲突和问题的核心。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只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作出更多让步,冲突就会得到解决,整个中东将立即变得和平而繁荣。
认真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常识”并不能解决中东地区数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的复杂关系。首先,和平的主要障碍常常被错误地描述为以色列不愿向巴勒斯坦人做出更多妥协。事实上,由于巴勒斯坦人一个世纪以来(有充分的证据)拒绝接受和承认犹太人民在其祖先家园的自决权利,冲突就一直延续不断。许多著名分析家出于某种原因忽略了这个重要的事实。此外,有效管理一个国家的基本要求是负责任的治理,审视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订以来巴勒斯坦人如何管理他们的领土(当时他们根据签署的协议接管加沙并实行自治),我们会发现: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建立很可能会给巴以双方带来更多的不幸。
历史证明,每一次以色列为了和平在领土和权力上向巴勒斯坦人让步后,后者都以恐怖和暴力作为回报。自1994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成立和2007年哈马斯暴力接管加沙以来,巴勒斯坦领导人在提供福利、安全、治理和法治方面辜负了其公民。其次,巴以冲突不是地区冲突的核心,解决巴以冲突不会对地区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只要国际社会只要求以色列负责,而不要求巴勒斯坦人负责,实现和平、安全和繁荣就没有机会,因为巴勒斯坦领导人已经表明,他们不会在犹太人祖先的土地上接受一个犹太国家的存在。
作为两篇系列文章的第一部分,本文将对巴以冲突的历史进行深入分析。第二部分将考察冲突对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
历史与和平的障碍
巴以冲突源于对同一块土地权利要求的冲突。然而,自从英国托管巴勒斯坦之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犹太人和以色列一再承认阿拉伯/巴勒斯坦人至少对部分有争议的土地享有权利,这是一个突出的特征。而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却一直拒绝承认犹太人民的权利,甚至在部分土地上自决的权利。
阿以冲突直到20世纪初才爆发。[1] 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圣地生活了数世纪,彼此和睦相处。自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罗马人摧毁以来,犹太社区继续居住在圣地,尽管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耶路撒冷、希布伦、采法特、提比里亚和加沙。历史记录显示,16世纪有2万多犹太家庭居住在采法特(今天的以色列北部)附近。[2] 自18世纪以来,来自欧洲的极端正统派老犹太人不断涌入以色列,希望在以色列地去世。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曾报告说,犹太人是耶路撒冷的主要居民。[3] 与欧洲各地犹太人的痛苦相比,分别经历穆斯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犹太人,以及生活在后来由国际联盟授权英国托管下的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均过着相对和平的生活。
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人寻求在圣地建立一个国家的现代民族运动,它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移民浪潮始于1882年,一直持续到1903年。一些阿拉伯领导人对新移民表示欢迎。1918年,麦加沙里夫侯赛因·本·阿里在麦加的官方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巴勒斯坦为“其原始子孙神圣和心爱的家园,”这意味着犹太人回到这片土地,将为他们的“兄弟”—阿拉伯人带来好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19年巴黎会议之前,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4]
然而,巴勒斯坦的大多数阿拉伯领导人和社区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愿望。但有些人是诚实和坦率的。1899年,耶路撒冷市长优素福·迪亚·哈立迪(Yusuf Diya Pasha al-Khalidi)写信给法国的首席拉比,试图说服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不要坚持在巴勒斯坦定居犹太人。他认为穆斯林和基督徒永远不会允许犹太人建立国家,并建议犹太人到其他地方定居。但是,他也坦诚地承认:“谁能挑战巴勒斯坦犹太人的权利呢?上帝啊,从历史上看,这确实是你的国家啊。” [5]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转折点。英国政府于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人的民族家园”。这是世界大国第一次承认犹太人在圣地的民族权利。《贝尔福宣言》成为国际社会承认犹太人民族权利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920年圣雷莫会议(决定原属奥斯曼帝国领土归属的会议)支持了该宣言。1922年,国际联盟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巴勒斯坦托管的决议,重申《贝尔福宣言》。国际联盟决定,作为受任托管的英国有责任“确保犹太民族家园的建立”。
英国人的到来,以及他们对犹太人家园的承诺,激起了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20世纪20年代以来,历史文献表明,阿拉伯人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以及随后的以色列人陷入暴力和恐怖循环,拒绝国际公认的犹太人拥有自己国家的权利。早在1921年,巴勒斯坦的第一轮阿拉伯暴乱就发生了,当时阿拉伯暴徒袭击了雅法和附近的农场和村庄,在七天的暴乱和暴力中杀死了47名犹太人。第二轮骚乱爆发于1929年夏天,起因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关于犹太人在旧耶路撒冷哭墙(犹太人敬拜的最神圣的地点)和圣殿山外部敬拜的权利的争论。历史记录显示,骚乱从耶路撒冷蔓延到巴勒斯坦。暴乱的悲剧事件是对希伯伦犹太人的屠杀。阿拉伯暴民残忍地杀害了67名犹太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英国警察强迫幸存的犹太人离开希伯伦,此前犹太人在希伯伦已经连续居住了几个世纪。1929年的暴乱还终结了另外两个有百年历史的犹太社区—采法特和加沙犹太人社区的历史。[6]
尽管如此,新的犹太移民并不渴望在种族或宗教上净化这片土地,而是伸出了和平之手。犹太人购买和定居的大部分土地都是人烟稀少、干旱的沙漠。巴勒斯坦的大多数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流领导者、以及后来巴勒斯坦犹太人社区(以犹太事务局为代表)的领导者,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分享或区隔土地的妥协之举,尽管犹太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连续不断地生活了许多世纪。
1947年,大多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无论是在巴勒斯坦还是流散在外的犹太人,都支持联合国的分治计划,并因此承认了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接受其和犹太国家并存。然而,1948年5月,当阿拉伯邻国的军队入侵巴勒斯坦时,以色列伸出的和平之手仍悬在半空。入侵的阿拉伯国家阻止联合国大会分治巴勒斯坦决议的执行,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
战争结束时,约旦哈希姆王国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埃及占领了加沙地带。停战协定确定了边界的划分。在阿拉伯各方的坚持下,各项协定规定,由于阿拉伯国家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存在,停战分界线将不被视为国际承认的边界。1967年阿拉伯国家耻辱性的战败强化了这种立场。1967年战争后不久召开的喀土穆阿拉伯联盟峰会发布了”三不”原则:“不与以色列和平相处,不承认以色列,不谈判…”即便如此,以色列也给予约旦以尊重,给了约旦监督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犹太人的权力。
1993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为巴以关系开辟了新的篇章。自协议签署以来的30年,历史记录表明,以色列为建立和平而作出的让步和措施换来的是新的暴力和恐怖浪潮。在《奥斯陆协议》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成立之后,发生了一系列自杀式恐怖主义事件(1994-1997年),造成15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第二次阿拉伯大起义(2000-2005)是在2000年8月戴维营峰会破裂后开始的,当时巴拉克总理向阿拉法特主席提出了一个被外界认为“很慷慨”的提议。在此期间,有600名以色列人在对公共交通、咖啡馆等的自杀性恐怖袭击中身亡。仅在2002年,就发生了近50起自杀式爆炸袭击,238名以色列人丧生,数千人受伤。
以色列2005年8月的加沙撤离计划要求拆除21个以色列定居点,其中居住着8000名以色列人。以色列给巴勒斯坦人留下了商业和农业基础设施,包括种植水果和蔬菜的先进温室。但它们很快就被巴勒斯坦人毁掉了,加沙地带也成了哈马斯和其他恐怖分子的避风港。2005年以来,以加沙为基地的恐怖分子向以色列领土发射了数万枚火箭弹和迫击炮。2008年,在奥尔默特总理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提出和平建议后不久,来自加沙的火箭弹袭击加剧,迫使以色列发动“铸铅行动”。考虑到如此糟糕的历史,以恐怖主义 “回报“以色列推进和平进程的努力,我们必须理解以色列不愿意推进和平进程的原因。
此外,巴勒斯坦领导人和公众仍然没有接受犹太国家的存在。尽管以色列的左、右、中派系领导人都承认巴勒斯坦人拥有建立自己国家的固有自决权,巴勒斯坦人公然拒绝回报,不承认国际法确立的原则,即犹太人民也有权在其祖先的家园享有自决权,这是联合国决议所承认的,正如外交部长王毅指出的那样,这是重要的指导方针。巴勒斯坦领导人似乎没有改变他们长达一个世纪的立场,罔顾历史事实,拒绝在他们认为完全属于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7]
以色列对官方认可的巴勒斯坦媒体中普遍存在的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的煽动行为,以及巴勒斯坦学校课程(从幼儿园到12年级)中精心安排的仇恨教学很是担忧,此种做法只会加深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导层不愿与以色列保持和平的警惕,除了正式条约,他们什么都不指望。巴勒斯坦媒体和社会对恐怖分子,包括奥斯陆协议签署之后对自杀式爆炸者的美化,他们的家庭不断得到财政支持,都受到欧洲捐助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组织的批评,这是反复出现和众所周知的。西岸难民营的一个青年中心以第一位巴勒斯坦女性自杀式炸弹袭击者瓦法·伊德里斯(Wafa Idris)命名了一场足球锦标赛,这只是众多事例之一。2002年,伊德里斯在耶路撒冷中心实施了自杀式爆炸袭击,杀害了一名81岁的男子,伤及150名平民。
在巴勒斯坦教科书和官方媒体中有许多仇恨言论和反以色列和反犹主义语言的例子。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官方电视台(PATV)播放了巴勒斯坦女孩歌唱犹太人是“猿猴和猪的儿子”的画面。2012年,法塔赫(阿巴斯总统的政党)在PATV上播出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耶路撒冷穆夫提谢赫•穆罕默德•侯赛因(Sheikh Muhammad Hussein)的讲话。仪式主持人邀请穆夫提上台说:“真主的话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与猿猴与猪的后代的战争是一场有关信仰的宗教战争。”
巴勒斯坦人不断的煽动和仇恨言论所引发的问题要深刻得多:“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能与那些憎恨它”并说他们决心摧毁它的人签署协议吗?大众对恐怖分子的公开赞扬以及对犹太人和以色列人公然和普遍的仇恨使人严重怀疑任何和平协议的可行性。
诚然,以色列社会本身并非完全不受反巴勒斯坦/穆斯林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的影响。然而,个别以色列人的恶劣孤立事件与巴勒斯坦人官方支持的行动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在以色列,种族主义、仇恨言论、煽动暴力和仇恨犯罪只存在于社会的边缘,而在巴勒斯坦社会中,这些特征是主流,得到了阿巴斯总统政党的一些巴勒斯坦领导人的支持,并在学校和夏令营课程中公然教授。
国际社会可能认为消除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仇恨教育和煽动暴力的担忧很容易。但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恨仍然是硬币的另一面,一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拒绝犹太民族在圣地自决是冲突的核心,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障碍。
此外,即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领导人能够在解决冲突方面取得进展,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政治现实仍然是主要的绊脚石。自2007年以来,巴勒斯坦领土实际上被划分为两个实体:(a)巴勒斯坦权力机构(PA)在巴解组织和法塔赫的统治下管理的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b)哈马斯统治的加沙地带。这种分歧反映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巴解组织领导层与哈马斯领导层之间的深刻分歧。哈马斯被西方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衍生机构,致力于对以色列发动圣战,以一个伊斯兰酋长国取代以色列。巴解组织本质上是一个世俗的民族运动。巴解组织参与了恐怖活动,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下,最近的一次是2000-2002年的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然而,阿巴斯主席致力于与以色列进行非暴力和安全合作,他也已将这一立场付诸实施。尽管阿巴斯公开了其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信念,继续为恐怖分子的家人提供资金支持,某些情况下还鼓励暴力示威,但阿巴斯一直坚持反对恐怖主义。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巴解组织是死敌。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哈马斯在各自控制的地区都面临着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哈马斯的统治是一场正在发酵的人道主义灾难,失业率接近世界纪录。它将可支配的资源用于恐怖活动和武器,而不是着手应对加沙的糟糕局势。约旦河西岸的社会经济状况要好得多,但阿巴斯总统和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国内力量薄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安全机构一直在镇压民众抗议,但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认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腐败,要求阿巴斯辞职。
正如最近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暴力冲突所表明的,哈马斯的最终目标是将其权力和控制从加沙延伸到约旦河西岸。阿巴斯总统取消了议会选举,因为他知道,巴勒斯坦公众的投票会把他和其政党选下台,转而推选哈马斯。鉴于上述情况,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巴勒斯坦国只会产生更多的灾难、暴力和绝望。
虽然如此,以色列仍希望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以国际法相关规范和原则协助双方实现和平,此外联合国确认以色列作为国际公认的犹太人国家,有在和平与安全的环境中生存的合法权利。同样,以色列拥有自卫的权利,国际社会应当坚决反对巴勒斯坦的恐怖主义、煽动暴力、仇恨言论和反犹主义。
翻译:关媛
[1] Alan Dowty, Israel/Palestine. 2nd 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 2.
[2] Palestine Royal Commission Report (Peel Report), London His Majesty´s Stationary Office, 1937, pp.11-12. And Leo Trepp (2001). A History of the Jewish Experience. Behrman House, Inc. p. 122. ISBN 978-0-87441-672-5.
[3] Shlomo Avineri quotes a report by Karl Marx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Daily Tribune on March 18, 1854 that of the 15,500 residents of Jerusalem, 8000 are Jews. Shlomo Avineri, “The Roots of Zionism,” The Wilson Quarterly, January 1983, p. 58.
[4] Quoted in Isaiah Friedman, Palestine, a Twice-Promised Land: The British, the Arabs & Zionism: 1915-1920.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0, p. xlvii.
[5] Neville J. Mandel, The Arabs and Zionism Before World War I. Los Angeles &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 47. See also Alan Dowty, Israel/Palestine. 2nd ed.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p. 63-64.
[6] Report of the Palestine Commission on the Disturbances of August, 1929. London: H.M. Stationery Office, 1930, p. 490.
[7] For a review of the diplomatic machinations concerning the “Jewish State” question, see Raphael Ahren, “Abbas Rebuffed Bid to Find Mutually Acceptable Wording on ‘Jewish State’,” Times of Israel, May 1, 2014 http://www.timesofisrael.com/abbas-rebuffed-bid-to-find-mutually-acceptable-wording-on-jewish-state/ [retrieved: May 28, 2021]. Tal Beker, the Deputy International Law Advisor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nd a member of Minister Livni’s negotiating team authored a thorough legal and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Jewish State” issue. See Tal Beker, “The Claim for Recognition of Israel as a Jewish State: A Reassessment,” Policy Focus #108, Washington, D.C.: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February 2011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claim-recognition-israel-jewish-state-reassessment [retrieved: May 28,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