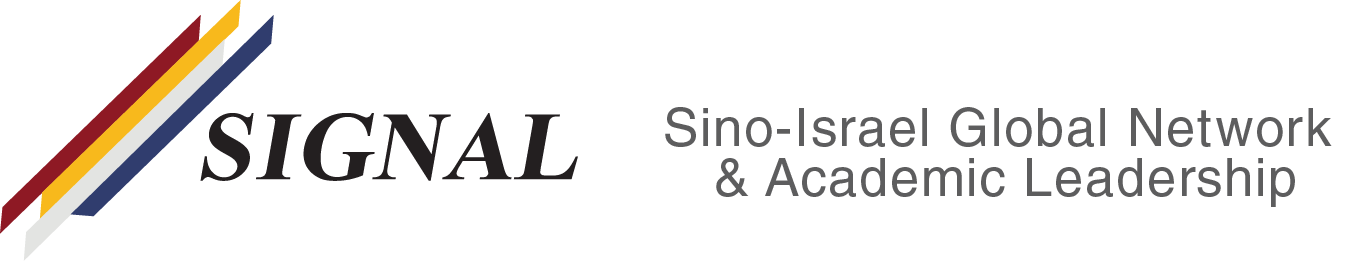Note 104 – 新故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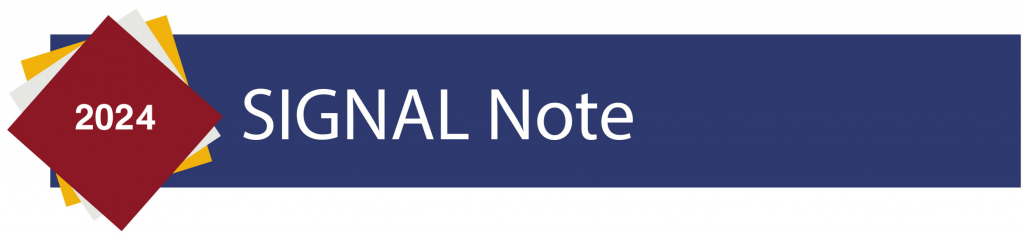
作者:(1902年10月30日)西奥多•赫茨尔 第一卷 一、 在阿尔塞格伦的咖啡馆里,弗里德里希·洛温伯格博士坐在一张大理石圆桌旁,陷入了深深的忧郁之中。这是维也纳最迷人的咖啡馆之一,,从学生时代起,他每天下午五点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例行公事般准时。那个体弱多病、脸色苍白的侍者顺从地向他打招呼,他也会很有礼貌地向同样脸色苍白的女收银员鞠躬,但他从来没跟她说过话。 之后,他会坐在圆形书桌旁,边喝咖啡,边阅读服务员递给他的报纸。在读完日报、周刊、漫画和专业杂志后(这绝不会少于一个半小时),他会和朋友聊天,或者独自沉思。 他曾在这里与伙伴开心聊天,现在却已烟消云散,只剩梦想。他习惯与两位好友在这共度美好闲适的夜晚时光,但他们已经在几个月前去世了。这两位的年纪都比他大,海因里希在将子弹射入自己太阳穴之前写道,他们比弗里德里希更早屈服于绝望,这按时间先后顺序也是合理的。奥斯瓦尔德前往巴西帮助建立犹太劳工定居点,在那里死于黄热病。 几个月来,弗里德里希就一直独自坐在他们那张旧桌子前。现在,他面前的那摞报纸也见底了,就直盯着前方坐着,也不找人说话。他觉得自己太累了,不想再结交新朋友,仿佛自己不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而是一个经常与珍爱的朋友分离的白发老人。他的目光紧紧盯着遮掩着房间四周的淡淡烟雾。 几个年轻人站在台球桌旁,正握着长杆,果断击球。他们与弗里德里希同病相怜,但这些崭露头角的医生、新晋法学家、刚毕业的工程师们都不像弗里德里希那样郁郁寡欢。他们刚刚结束专业课程的学习,现在无事可做。他们大多是犹太人,除了沉迷于打牌、打台球,他们也会抱怨“这世道”出人头地是多么艰难。与此同时,他们又在无休止的牌局中打发着“这世道”。弗里德里希为这些不懂事的年轻人感到悲哀,但同时又相当羡慕他们。 实际上他们只是一种上等无产阶级,二三十年前一种观点盛行于中产阶级犹太人中,这种观点认为:新一代绝不能再走父辈的老路,他们将从辛苦的商业贸易活动中解脱出来。受这种观点所害,年轻一代全都开始了“自由”职业。后果就是,受过专业教育的人员过剩,就业困难,但他们又被体面的生活惯坏了,不能像自己基督徒同事们一样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可以说,他们成了市场上的毒品。尽管如此,他们仍承担着自己“社会地位”的义务,这是一种傲慢的阶级优越感,他们还需获得学位,这是一先令也换不来的。那些有点儿储蓄的年轻人逐渐花完了存款,或者就继续靠父母提供经济支持。另一些人则在寻觅合意的伴侣,希望能给一个有钱的岳父当牛做马,这样的前景对他们相当有吸引力。还有一些人在优雅体面的行当里进行一些无情的,并不总是光彩的竞争。这些年轻人因为不想成为商人,就以“专业人士”的身份从事秘密疾病和非法法律事务的交易,他们构成了一副奇怪而又悲哀的社会景象。有些人因为需要而成为记者,贩卖舆论。还有一些人为了扬名立万,拉帮结派、奔走于公众集会,吆喝着毫无价值的口号。 而弗里德里希不会做出以上任何改变。可怜的奥斯瓦尔德在去巴西前曾严肃地对他说:“你不适合生活”“你对太多事情感到厌恶,人必须能吞下东西,例如害虫或内脏,这样,一个人才能变的强壮,有血有肉,才能得以善终。可你,你不过是个高贵的混蛋。你还不如到庙里当和尚去!没人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因为你是犹太人…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继承的那几先令远撑不到你在法律界站稳脚跟,然后你要么被迫做一些你所厌恶的事,要么上吊自杀。我求你了,在还有一个基尔德(荷兰货币单位)的时候,给自己买根绳子吧。别指望我!一方面,我会离开这里。另一方面,我是你的朋友。” 奥斯瓦尔德曾哄骗他一起去巴西,但他一直未能下定决心。他没有告诉这位即将在异国他乡早逝的好友自己为什么拒绝。这个“理由”就是一位金发的、如梦般美妙的甜心。即使对这两位信任的朋友,他也不敢说起欧内斯廷,怕被他们取笑。现在他们已经离世,即使他想说,也再无处寻求安慰或建议了。他的处境十分艰难,如果他向他们诉说困境,他们将会说什么?假如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在三个人又一起坐在那张旧书桌前呢?弗里德里希闭上眼睛,想象着他们之间的对话。 “朋友们,我恋爱了,不,是我爱…”。 “可怜的家伙!” 海因里希会说。 奥斯瓦尔德却会说:“这么愚蠢的事像你的风格,亲爱的弗里德里希。” “哦,这可不仅仅是愚蠢,我的朋友们。这是十足的疯狂。如果我想让欧内斯汀•洛夫勒的父亲把她交给我,他可能会嘲笑我。我只是个律师助理,拿着一个月四十基尔德的薪水。除了一无所有还是一无所有。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一败涂地,花光了最后几百基尔德的遗产。我知道让自己一无所有是很疯狂的,但我想靠近她…欣赏她优雅的姿态、聆听她甜美的声音。我必须去她夏天住的温泉疗养院,那里有戏剧、音乐会和其他一切活动。在那样的场合中,男士必须穿着体面。现在,我一无所有,但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爱她。不,比任何时候都爱!” “那你想干什么呢?”海因里希问 “我想告诉她我爱她,让她等我几年,等我做出一番事业。” 奥斯瓦尔德尖刻的笑声回荡在他的脑海中,“是呀!是呀!等吧!欧内斯汀•洛夫勒会等到饿死。哈哈哈!” 弗里德里希的耳边居然真的有人在笑。他猛地睁开眼睛,是施夫曼,一位年轻的银行职员。他们在洛夫勒家见过,施夫曼站在他面前开心地笑道“您昨晚一定睡得很晚吧,洛温伯格博士,这个点还犯困!” 弗里德里希有些尴尬,回答说“我没睡着。” “好吧,又是深夜了。你肯定要去洛夫勒家了。” 施夫曼懒洋洋地坐在书桌旁的座位上。 弗里德里希对这个年轻人不感兴趣,但也让他做伴,因为他可以向他谈起欧内斯廷,还经常从他那里得知她要看什么演出。(施夫曼与剧院售票处的人有交情,能买到最热闹的演出票)。他回答道:“没错,今晚我也要去。” 拿起报纸的施夫曼突然惊呼道:“我说,这太奇怪了!” “怎么了?” “这则广告。” “啊,你也看广告啊!”弗里德里希一边说一边戏谑地笑了笑。 “我也看广告吗?”施夫曼反问道。”我特别爱看广告。除了证券交易所的报告,报纸上没有更有趣的东西了。” “是啊!但我从来不看证券交易所的报告。” “啊,是的,你…但只要我看一眼汇率,我就能把整个欧洲的形势总结一下……但看完汇率之后,我就立刻去看广告。你不知道那里有多少东西。有卖各种东西的,也有贩卖人口的。也就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花钱买到,但问题在于并不是每次都能买得起。我总能从广告栏发现什么机会。我的意思是:我什么都知道,却什么都不需要!……最近几天,我注意到一则引人注意的广告,但我看不懂。” “是用外语写的吗?” “嗯,看看这个,”施夫曼把报纸递给弗里德里希,然后指着一张小告示,上面写着:“招募,受过教育的绝望青年,愿意用生命做最后一搏。如有意愿,请联系:N. O.Body(博迪),办公室。” “你说得对,”弗里德里希说。“这则广告确实引人注目。一个受过教育,但是满心绝望的年轻人。当然有这样的人,但他的处境一定相当困难。只有一个人真的绝望了,才会用生命来做最后一搏。” “嗯,博迪先生似乎还没找到这么个人。他登广告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我想知道这位博迪先生是谁,他品味真独特。” “没有这么个人。” “没有这么个人?” “N. O. Body,连起来就是Nobody,在英语中指没有人。”“啊,好吧。我没往英语那方面想。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需要……不过,如果我们去洛夫勒家不想迟到,就该出发了。我们今晚一定要准时。” “为什么偏偏是今晚?” “对不起,我不能说!我向来非常慎重……但请准备好迎接惊喜……服务员!结账!” 惊喜?弗里德里希突然感到一阵隐隐的不安。 他和施夫曼离开咖啡馆时,注意到外门口站着一个十岁的男孩。那孩子的双肩蜷缩在一件单薄的小外套里,双臂紧紧地抱着身体,在一个避风的角落里踩着飘雪。他蹦蹦跳跳的,似乎在摆造型,但弗里德里希意识到,穿着这样单薄的鞋子,这孩子一定冻得很厉害。借着路灯的光亮,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三枚铜币。男孩哆哆嗦嗦地道了谢,然后跑开了。 “什么!你居然支持街头乞讨!”施夫曼愤愤不平地喊道。 “我觉得这小家伙在十二月的冷天里跑来跑去可不是为了玩……而且,他看起来也像个犹太小孩。” “那就让他去犹太社区或以色列安联,晚上别在咖啡馆闲逛!” “别激动,施夫曼先生。你什么也没给他。” “亲爱的先生,”施夫曼坚定地说道,“我是反贫困和乞讨协会的成员。每年都要交一基尔德的会费。” 二、 洛夫勒一家住在贡萨加街一栋大房子的二楼,一楼是莫里茨-洛夫勒公司的布行。 弗里德里希和施夫曼走进门厅时,看到挂在那里的大衣和披肩的数量如此之多,意识到今晚的聚会规模比往常要大。 施夫曼说:“衣服多的可以开家服装店了。” 弗里德里希与客厅里的大多数人都相识。唯一生面孔是个光头男人,站在钢琴旁,身侧是欧内斯廷,他正对着欧内斯廷自信地微笑着。 […]